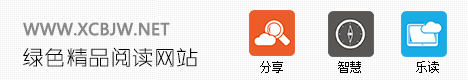突然就有人在门外对志平喊,你老婆被人打了,你还不赶快看看去。
听到喊声,志平的身体一抖,燥热的身体上仿佛刮过了一丝凉气。他正在做一块广告玻璃,手里拿着玻璃刀割得起劲,“秋老虎”还没有退却,作坊里闷热不堪,身上的背心被汗水洇透了,正往下滴着汗水。
他把玻璃刀放到铺面上,朝门口外的人随口问道,被谁打了?
臭勇。门外答道。
臭勇为什么打我老婆?志平又问道。
这谁知道?你问臭勇去。门外说。
志平放下的玻璃刀又迟迟疑疑地拿在了手里,嘴里低声沉吟,这臭勇,一个大老爷们儿和女人打得什么架?真是,枉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志平自言自语说着,又割起玻璃来,只是声音没有先前的平和和不紧不慢了,也失去了特有的节奏感。
“王记玻璃店”是桑梓路上的老字号了,说不上有多长的历史,但两辈人是有了,现在的老板志平却姓李。这没别的,志平是外来人,是王家的女婿。当年,志平从郊区来到桑梓路学徒,十六七岁就来到这王记玻璃店里,老王掌柜喜爱他的憨厚老实,手艺也是如数尽传。老掌柜的儿子春雷却不喜欢这行当,考上师范当了教师。老掌柜的手艺无亲可传,便让女儿春芽把志平招了上门女婿,老掌柜过世后,王记玻璃店的老板就姓李了。

桑梓路上的行当尽管五花八門,隐藏着高人能手,但这条路上是极太平的,可这太平的路上单单出了臭勇这么个混星儿,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还是光棍一根,有点儿“恶霸”的意思,街坊邻居都不惹他,他恶霸也恶不起来,春芽好端端的日子惹这货干啥?志平这么想着,日头就落下去了,本来这是每天停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故意磨蹭拖延了一下,今天能干完的活没干完,也无心再干下去了,便收拾店铺关门回家。
桑梓路不太长,只是居住的地方偏离些大路,志平走出门来,四周瞅了一眼,感觉挺平静,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说不定春芽的气已经消了,回家去了。
想到这,志平的心情就好了些,往家走的步子也灵便了,可走着走着,只见胡同头的小超市前还围满了人,好像有人还坐在地上撒泼。志平刚平复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随着他的脚步渐渐往小超市临近,他感觉自己的脸庞火辣辣的,仿佛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他,使他如芒在背。
走近了,围观的人为志平闪出一道缝隙,因为在地上撒泼的果然是他老婆春芽,春芽一见志平,一下子放声嚎啕起来,好像是溺水的人一下子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她的嚎啕中还带着骂,你这死不了的,到现在才回来,你老婆都要被人打死了,你也不管呀!
志平先伸手去扶老婆春芽,春芽哭着委屈地甩开他的手。志平便扭头向围观的邻居打听事情的原委。事情其实很简单,事也不大。秋老虎弥漫时,冰凉沁心的扎啤的销量就更好了,其实扎啤是岛城人抗击炎热的最好饮料。半下午,春芽估摸着志平快要回家了,下楼去给丈夫打扎啤,这也是每天的必修课,女儿上大学走了,照顾玻璃店的老公是她唯一的工作。春芽来到小超市里,活该今天太热,扎啤卖得太快,送货的还没来,扎啤桶倒了底也没倒出多少。小超市老板焦急地拨了通电话,又对春芽说,等等吧,送货的要七点后才来,要不你就多走几步到别处打。春芽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半下午了,艳阳依旧炙热,这样的天气走几步都出汗,真懒得去别处了,就说,你打吧,有多少就多少。小超市老板就去打扎啤,若在平时,春芽每天都要打二十块钱的,今天的也少不了多少,大约十三四块钱吧。老板说,对不起啦,管多少就给十块钱吧。春芽就把刚打的扎啤挂在了门把上,到钱包里去拿钱。
这时臭勇从外面走进来,越过春芽,往老板的面前扔下十元钱,随手摘下了挂在门把上的那袋扎啤。
你干什么?我买下了啊。春芽说。我先交的钱。臭勇说。小超市老板也拾起面前的十元钱还给臭勇,说,这酒是春芽的,你稍走几步到别处买吧。臭勇不知哪来了气,猛地把眼一瞪,我的钱不好用吗?说完,提着酒转身就要走人。
春芽急了,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怎么欺行霸市啊?
我不做买卖怎么能算作是欺行霸市?臭勇依旧圆圆地瞪着眼,怎么?你这臭老娘们儿还要动手吗?我就不给,别人还行,你凶什么?就叫你今晚喝不成酒。
春芽是桑梓路上的老人啦!以前哪吃过这样的亏,受过这样的气?!在臭勇的面前并不示弱,你叫街坊邻居评评理,声音就大了起来,语言的内容也就不干净,骂人的话从嘴里蹓跶了出来。春芽开始骂人了,春芽的骂人在桑梓路上很有名,她的骂声的直接承受者就是志平,她骂人的语言不但尖锐,而且内容广泛,涉及的面广,在她嘴里,臭勇、臭勇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他的祖父母或有或无的事都成了春芽骂人的佐料和素材,一时间臭勇的祖孙八代有了一部罪恶史,让任何人都会羞愧、都会屈辱。
臭勇真的无地自容了,冲了上去,揪住了春芽的头发……
这小子真不要脸,太欺负人了。听完街坊邻居的诉说,志平也双眼圆睁,咬牙切齿地说,真不能轻饶了这小子。
算了吧,都街坊邻居的,小超市的老板过来劝道。
这事放在你身上你能忍受的了?志平怒气不减。
众人都看着志平,看着他满脸怒气地过去拉起老婆春芽,走,先回家。
桑梓路上要有架打了。众街坊邻居看着志平的背影,想像着他那怒气冲冲的表情,三五人在一起议论,在一起交头接耳,看志平那样子,这事儿能罢休?治治臭勇这号人也行,要不然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以后要上天了不成?
志平嘴上虽这么说,但要怎么做?心里却没有底,他在桑梓路住了这么多年,一直老老实实地、忍气吞声地做人,从未和任何人红过脸打过架,出现了什么言差语错的事,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这事该怎么去处理呢?
志平在扶着春芽上楼梯时,脸上的表情正向平和恢复,心里就琢磨着该怎样劝劝春芽,这事忍一忍过去就行了。
可两人走到三楼楼梯口时,正好与下楼的邻居碰了个对面,平日里都打招呼的,今日偏偏却只是微微笑了笑。志平突然觉着这笑别有意味,他的眉头一锁,马上表现出刚才的怒意。
你准备怎么去收拾这臭勇?两人刚进门,春芽就问志平。
志平的身子猛一哆嗦,他没想到春芽开口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事儿,这话竟一下子戳到了他的软处,他故作深思状,上前抚了一下春芽的背,又摸了一下春芽的手,低声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必去计较一时的痛快。
你这个窝囊废,我早就知道你有这出……春芽猛地爆发起来,若不是你整日这么软弱,臭勇敢骑在咱们的头上撒尿拉屎?
春芽的火气已由臭勇的头上转移到志平的身上,骂的对象也由臭勇变成了志平,志平又畏缩在角落里不吱声了。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志平一下子找到了借口,急忙起身去开门。门开了,门外站着小舅子,春芽的弟弟春雷。志平开了门还故意探出头去向春雷的背后张望,在楼梯的拐弯处,他看到了几个急匆匆躲避的背影。
别看了,进去再说。春雷说。志平便退回来,和春雷一起进了屋。
弟弟春雷来了,春芽便不骂了。但是心情受了委屈,坐在那里没动。志平便到厨房里忙活晚饭,心里说幸亏春雷来了,要不然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哪?志平听不清姐弟俩说什么,但他想征求一下春雷的意见,让春雷劝一劝春芽,事过去算了,便找借口想把春芽支出去。忙活了一会儿,探出头来对春芽喊,春雷来了,你出去打扎啤去!一听扎啤两字,春芽一惊,像炸了似的跳起来。志平的心猛地一悬,怕又要坏事儿,让他没想到的是春芽这次没有开骂,而是进了厨房,你去打,我做饭。看来,扎啤留下阴影在春芽的心中还没消去。
志平出去打酒,走在桑梓路上,他有些不自然,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他,让他感觉到一切都不再像以前。他故意走得很慢,在路上消磨时间躲避春芽的数落——回到家时,饭菜已经上桌,四菜一汤,单等这扎啤。
几杯酒下肚,春雷稍有酒意,他抬起头来对志平说,姐夫,这事不能算完,不能这么轻易便宜了臭勇,你得争口气,刚才我来时,你家门前就围了听话的人,大家都在看着你哪!再说,这事儿放在我身上也不行,我是桑梓路上的大学生,是有身份的人,难道还会怕臭勇这么个地痞?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志平就蹲在臭勇家的那座旧楼前,双眼紧盯着臭勇家单元间的楼道。这个举动,是志平一夜彻底不眠的结果,他头发蓬乱、双眼血红,一脸的愤怒。
志平脸上愤怒,心里却满是埋怨。臭勇啊臭勇,你也称得上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上过山,下过海,穿过街,走过巷,怎么能和一个长头发的女人过不去呢?较什么真啊?孔夫子都说,好男不和女斗,你呢?算什么好汉?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找我,在我面前有什么事過不去的?
天光渐渐亮堂起来,桑梓路上赶早市的人已经零零散散地来往。人们看到蹲在楼洞前的志平,心里都暗暗为他捏把汗,看到志平的表情,他们或许嗅出了味道,脸上马上荡漾出一股兴奋,转过身去眼巴巴地等待着剑拔弩张的那一幕。
天光大亮,志平的胸口一热,心狂跳不已,一下子蹿到了嗓子眼儿上,臭勇?是臭勇!志平揉了揉眼睛,确认是臭勇出来了,手里提着个篮子,看样子是要去赶早市的。这家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去赶得哪门子早市?难道又勾搭了新的女人?
志平心里又隐隐担忧,会不会因为他找臭勇论理耽误了他的好事?不会为此把他的新女人搅黄了吧?志平想着,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臭勇叼着烟卷走了过来,志平迎上去,臭勇却吐了个烟圈,迎上前拍了拍志平的肩膀,兄弟,起来了。说完,摇晃着身子过去了,留给他一个迷惑的背影。
这臭勇,难道不知道我找他,昨天打人的事就这么过去了?志平呆呆地站在地上,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臭勇这种态度,一时还真让他手足无措了。
他妈的,这臭勇真不是东西。志平在心里骂,大伙儿也在嘴上骂,有人上前给志平出主意,要不干脆把春芽送到臭勇家,反正他打了人,让他管吃管住地伺候着春芽,臭勇又刚换了新女人,正好有人伺候,说不定还能把他这新女人给搅黄了。
志平的脑袋里嗡嗡的,像是塞满了棉花,他真拿不出主意了,只好怏怏地回了家。
傍晚时分,春雷又来了,志平呆在家里,生了一天闷气没出门。春雷一见志平的样子表情就极其不屑,你这样做有用吗?
那你说怎么办?我带着刀去找他拼命吗?志平也把肚子里的愤懑发泄出来。
用得着吗?一看就是土匪做法。春雷说,报警,让警察去对付他。
这好吗?都邻居街坊的。志平说。
怎么不好?他动手打人还顾邻居街坊了?春芽接话说。
三人合计,方案确定下来,报警。
第二天早上,志平带着春芽去报警。出发时,他表现得很悲壮,很英勇,面上的表情很庄严。
这是去干啥呀?怒气冲冲的。小超市老板看到他们的样子,疑惑地问。
报警哪!志平严肃地说,老子不能便宜了臭勇这小子。
小超市老板表情也一惊,这可是他从来都没想到,他急忙从小超市里走出来,仿佛这事发生在小超市,和他也有很大关系似的,上前劝道,都街坊邻居的,用得着这样吗?不如找街坊串通一下。
还串通什么?你看臭勇,还有人样吗?不治治他行吗?志平依旧严肃地说。
志平就拉着春芽去派出所报案。桑梓路上没有派出所,要到芙蓉街道。桑梓路平时都是很太平的,和派出所就没打过什么交道。
去的时候,早就过了上班时间,但是派出所的铁门却紧锁着。是事太多还是天下太平呀?志平心里嘀咕着上前拍打铁门。手拍在铁门上,回响声咣咣的,不见回,就又拍,这声响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挺烦人的。
干什么的?里面终于有了回响,是警察们惯用的那种声调。报案的。声音是鲜明的对比,志平怯怯的。怎么啦?里面没人出来,好像有什么事,只是往外面传话。
打人啦。志平依然很胆怯。
什么时候打的?
昨天。
昨天打的,怎么现在才报案?当时为什么不打“110”?现在怎么取证?先去医院吧,到医院去诊断治疗吧,治疗好了再过来备案处理。终于有人从铁门里探出头来,给志平支着招,说话时,警察眼睛瞅着春芽,好像从春芽身上看不出曾经挨打的痕迹。
对,看来还是要到医院去取证的,没有医院的诊断怎么能说春芽挨过打呢!志平想想也对,就问那年轻警察,去什么医院算数?
正规医院就行。就近去社区医院检查就行。你们这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等治疗好了,我们给调解调解。年轻警察说。
警察的话给志平指点了路途的步骤,志平就直接去了社区的医院,如今得病的人仿佛多了,大热的天就这么小小的医院大厅里坐满了输液的人,表情各异,眉头紧锁的,愁眉苦脸的……惟有医生的办公室里传来了男女医生的嘻闹声,男的说昨晚喝的大酒,女的却文不对题地说昨天去看电影,里面的女主角腰是腰,腚是腚,而男主角是丑八怪,也不知女的喜欢男的什么地方,难道是那方面勇猛?好白菜被猪拱也有拱的道理。女的话挺碎,说得露骨,连春芽这样泼辣的女人听了脸都有些发烧,这年头说话也不忌讳外面这么多病人。
志平和春芽循着声音走进去,医生办公室里三个人,男的秃头,女的年轻,还很漂亮,志平心里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怎么能说出这么下流的话?
秃头医生倒是很热情,一见来人急忙站起来迎上去,等志平讲完了原因,就更热情了,笑嘻嘻地安慰说,这样事呀,不要着急,住下来安心治疗,保证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房间,不让行凶者付出惨重的代价是不解气的。
秃头医生很会抓人的心理,话说得很贴春芽的心,听着顺耳。秃头医生戴上听诊器,准备装模作样地为春芽诊断,转头对志平说,你去交上住院押金。志平脸上一红,探头问,交多少?看着交吧,一千元垫底。秃头医生说。志平和春芽早上出来并没带太多钱,两个人凑了凑,共八百元,志平手哆嗦着握着钱问秃头医生,只凑了八百……王记玻璃店这么多年的老字号,没钱?秃头医生不相信,没带……春芽接话说。秃头医生扭头看了眼春芽,明白主事儿的在后面哪,先凑合交上吧。志平去交钱,几个人便围着春芽忙碌起来,社区医院虽小,但设备科目齐全,验了血,做心电图,做CT,检查了一番后,然后开处方,取药,把春芽领进病房里输液……做完这些手续,护士就通知说押金不够了,要志平续交。
春芽对志平说,你回家去拿钱吧!志平站着没动,等护士退出去,才支支吾吾地问,钱在哪?春芽顿了顿,没吱声,想了一会儿又说,还是输完液我回去取吧,反正我来回走没问题。你回去取不行,你明明在住院,再回家蹓跶,让人怎么说?志平说。春芽想想,把志平的头扳到跟前,附在耳朵上叽里咕噜了一番,最后用手指着志平的脑壳,只准拿一千,要是多拿一分,看我出院怎么收拾你。志平嘻嘻地笑着,加一百元的零花钱吧?春芽面色一沉,你要钱干什么?有歪心?志平的嘻笑被噎回去,低声说,你在住院,我得花钱给你买饭吧。你兜里没钱?春芽问。志平说,买扎啤花光了。志平声音依然小。先拿一百吧。春芽说。
志平像得到圣旨似的离开了。回到桑梓路,路过小超市前,有几个闲散的邻居正聚堆儿在门前下棋,见了志平,小超市老板问,怎么样啦?
志平挺了挺腰身,有点儿大义凛然地说,报案了,春芽住院了!说完,志平又用力挺了挺胸,径直往前走了。
报案?住院了?聚堆儿的人听到这样的字眼都抬头望着志平远去的背影,怕是真要要臭勇的好看。
医院里的人都很同情春芽,说这臭勇太野蛮了,一点儿道理都不讲,绝不能轻饶了这家伙。春芽听了心里更加委屈,接着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秃头大夫更是热情,每天都到春芽的病房问询检查,白大褂飘飘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挺像回事。
在医院里住了四天,春芽嚷着要出院。这几天恢复得很快,容光焕发。志平去找秃头大夫,说,好了,就出院吧。秃头大夫说,怎么现在就出院,虽然身上的伤好了,但是精神上的刺激还没恢复好。志平回去对春芽说,春芽把眼一瞪,精神个屁!出院。志平知道,春芽是心疼钱了,虽说是在惩罚臭勇,将来钱会由臭勇出,但是现在垫钱也很心疼,每天都交,一天一千元,什么家底敢住時间长了。一天的费用顶他开近十天的店,再说,志平照顾春芽,又要操持家务,挺忙的。志平心里也痛,刚要去办出院手续,春雷打电话来询问姐姐春芽住院的情况,一听要出院,口气马上变了,出什么院?就在里面待着,垫点儿钱怕什么?到时候把住院费用往臭勇面前一摊,看他敢不拿。我询问了,公安局不行,还有法院,不信法律治不了他。姐夫也不用去店里,到时候连误工费他也要付。春雷的话对春芽有作用,只好暂时打消了出院的念头,在里面恢复起了精神。
玻璃店都关门好几天了。一些客户便按店面上留的电话来询问。志平就说,春芽被打得住院了。
伤得重吗?客户问。
医生说挺重的。志平说,不重怎么能住这多日子?
公了还是私了?客户也是邻居,臭勇这人挺无赖。
私了不了了。志平说,已经报了案,他耍无赖到公安面前耍去。
志平每天路过桑梓路回家做饭,再提着饭回到医院,在路上好几次碰到了臭勇,他的心里都慌慌的,他心里盼望着,臭勇能主动走上前来,主动问问这件事。可是臭勇没事人一样,故意扭头不看志平,一脸傲然地走了过去。
志平对这件事没了底,心里虚虚的。按理说,志平报了案,春芽住了院,一招一式地都动了真格的。臭勇就应该主动来医院赔礼道歉,两家协商把这事解决了就行了。可是臭勇对此事的不理不睬让志平骑虎难下,再在医院里住下去,医药费越积越多,万一臭勇真赖着不出,再灰溜溜地回家,这不是自打耳光、自取其辱吗?
志平把内心的顾虑讲给春雷听,春雷对此不以为然,怕什么?他臭勇能赖得过法律?到时候强制执行。
到了第十天,春芽真在医院里待不住了,垫出去的钱扎到她心了。志平也坚持要出院,一天天累积的医药费让他忐忑不安,钱越多越难要的。秃头大夫一丝不苟地检查,查出春芽患上了盆颈炎,这种病是因为被打心情压抑所致。
春芽要出院,秃头大夫有些遗憾。当然在这十天里,他也了解了一些臭勇的情况,不自觉地给春芽用的药就少了,他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异样和不同往常。以前遇到打架斗殴的,都是个赚钱的病号,被打的一方赖在医院里死活不出院,一味地多用药,用好药。而打人的一方总是来找医生,求情,送红包,都望医生手下留情,给省点儿钱……可自从春芽住院以后,都十天了,打人的臭勇连面都没照,这事儿就有些蹊跷有些悬了。
住院十天,花了八千三百多元。志平领着春芽又到了派出所去,这次派出所的民警接待了他们,做了笔录,也收下了药费单据。青年民警说,我们会通知臭勇,把这事儿调解调解。
调解调解?志平对民警的用词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警察不抓人?
没到那个份上,我们会传唤他。现在都是文明办案,以前那一套不行了。
志平和春芽将信将疑地离开了派出所,心里安慰的是警察说他们会传唤臭勇,他们不知道“传唤”是什么意思?但是听起来像个法律词汇,挺吓人的。
王记玻璃店又开门了,但是志平的心思却不在割玻璃、烫玻璃花上,而是时时刻刻注意着桑梓路,时时刻刻在注意着桑梓路上的动静,臭勇是怎么被传唤的,被警察带走了吗?
可是这臭勇依然在桑梓路上摇摇摆摆地走,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有时听到马路上响起警报声,他明明听出是救护车的声音,也要从店里跑出来,望着车的背影一脸的失望,臭勇还在摇摇摆摆地走。
大约又过了十多天,派出所警察给志平打来电话,让他到派出所去一趟。志平悬着的心落了地,他的心情舒畅了,事情终于有了结果。
又要去哪?见志平关门,有人禁不住问。
去派出所,要处理这事了。志平大声说。
志平去的时候趾高气扬,回来时却垂头丧气,警察对志平说,他们传唤了臭勇,调解了,但是臭勇死活不出这钱。
那警察不能抓人吗?志平问。
不够条件呀!现在都是文明办案,警察也不能随便用强制手段。要钱?你们起诉吧,法院才能判决执行,到时,派出所可以提供所有的证据。警察说。
志平就这么回来了,一路想着心情越来越不好,就打电话给春雷,把警察说的话又传了一遍。春雷听后,等不及下班就赶了过来,他说,起诉以前,咱们俩去找他一次,给了钱就完事,不给就起诉。
志平和春雷去找臭勇,谁知臭勇一脸的不屑,说,警察找我了,我不给,谁让你们去医院的?爱找谁找谁去!别来找我。
春雷说,臭勇你不要这样横,因为我们是街坊邻居,才来找你,你若态度好,愿出医药费,花了八千三,我们可以商量着让一点儿,要是真告到法庭上,就没有余地了,你掂量着办。
去法庭告吧!臭勇依然不屈,到时候法院要什么就给什么,要我的头我也砍给你。
好,那就法庭上见。春雷说完拉着志平扭头就走。说到打官司起诉,志平心里直犯嘀咕,街坊邻居打官司能有个头吗?俗话说,屈死不告官,提到法院心里就都战战兢兢的。志平说,这官司能赢吗?别到最后打不着狐狸惹了一身臊!
现在官司不打是不行了,这是要争口气。春雷说,要不被人欺负成这样,在桑梓路上还怎么过下去。
成,就打官司,告吧。志平下了决心。说是打官司,可怎么个打法还真理不出头绪。志平和春芽去了法院,打听着找到了立案厅,里面人还挺多,没有想象的那么严肃,人来来往往的像赶集似的。志平的心里释然,原来的纠结平复了,来法院打官司的并不是他自己呀!立案厅里忙碌还有个原因是正施工,正在把柜台上面的铁栅栏拆下来,原来里面的法官和立案的人是隔开的。办公桌前的法官两男一女,面无表情,每个人前都排着长队,他们机械似的敲打着键盘。志平让春芽坐在条椅上等,他去排队,前面有个青年人提着黑提包,面相挺和蔼,志平就搭讪,你也来立案呀?青年人点点头。立案的人也挺多啊!志平说,现在事多,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强了,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了。青年人微笑着。
青年人的笑拉近了志平与法院的距离,打官司的人也都不一定是苦大仇深。一会儿就排到了志平,女法官头也不抬,直接伸过手来,志平茫然,四周扭头,不知她要什么?女法官手伸累了,問,诉状呢?什么诉状?志平更茫然。没诉状立什么案?女法官说着从一沓信笺上撕下两页纸递给志平,说,写好诉状再来,下一位。志平就被挤到一边。志平看着手里的纸,上面是黑字黑格:起诉书?他连封信都写不全,哪会写起诉书。幸亏有个上过大学当教师的小舅子,就又给春雷打电话。
春雷一听,在电话那头笑了,姐夫,你傻吗?你这是什么话?志平不高兴了,就让他帮忙写个诉状怎么就傻了?你写不写?
我写不了。春雷说,现在官司哪能一个人打?要请律师的,不请律师,立案也得好几个月,现在案子多如牛毛,没有律师怎么行?我给一个律师打个电话,你去找找他。
请律师花钱不?志平问。
你真是,海都过去了还怕条小河。春雷“切”了一声。
律师竟然是排队时的青年人,姓李,让志平称他小李。小李看在春雷的面上,代理费只收了一千五,加上起诉费五百,又二千元拿了出去。
又过了一个多月,小李律师给志平打来电话,说法院法官明天要来桑梓路,要来现场调查取证。志平手握电话激动得不行,忍气吞声了这么久,或许真的要有个结果了。志平激动了一会儿,觉着这样不行,小李律师光把电话打给自己哪行啊?
志平思忖了一会儿,又鼓起勇气给小李律师打了电话,李律师,明天法官真的要来桑梓路啊?
对,不是刚电话告诉你了吗?小李律师不解。
李律师,你看能……不能把这事……告诉小超市的老板……让他转达给……志平说,就说给我打电话没打通。
为什么呀?小李律师问,再说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我发信息给你。志平说,麻烦您按我说的做吧。
电话那头,小李律师顿了一会儿,说,好吧。
志平的嘴角露出了笑意,在关电话时,他隐隐地听到小李律师在低声自语,真是莫名其妙……
傍晚,志平从玻璃店回家,快到小超市时他故意放慢脚步,生怕引不起小超市老板的注意,错过了时机。志平走,故意目视前方,只是用余光去瞄小超市的老板。
志平,律师来电话让我转告你,法官明天来调查取证啊!果然,小超市老板对他喊。志平就站下来,是么?这律师怎么不给我打电话?真是。他说你的电话没打通。真是的,我整天都开着机的。志平说。
既然电话打到了小超市里,那法官来调查取证的事,整个桑梓路也就都知道了。大家都在感叹,志平真有骨气,真打起官司来了,是得治治臭勇,给桑梓路的人出口恶气。
志平,官司打赢了,请客啊!有邻居冲他喊。
行!请客吃饭人太多,我给咱们社区请三天电影。志平说。
电影和唱戏都行,大家聚在一起就行。邻居说。
是啊!志平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欣喜,貌似平静,内心却是冤屈和正义即将得到伸张的兴奋。
志平和春芽激动得一夜无眠。清晨,志平没有去玻璃店开门,而是从里到外打扫了卫生,春雷也请了假来等待,志平和春雷合计该到哪家酒店请法官和律师吃饭。
整整一天,春雷身着正装,在桑梓路来回地走。志平和春芽还到路口去看了两三次,志平更在意的是臭勇此时的表现:他是不是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惶失措呢?志平上路口看小李律师和法官时,看到臭勇正在楼道的阴凉里下象棋。志平不动声色地走过去,若无其事地蹲下身去,他对象棋略通一二,他看到臭勇的棋已陷入困境,无力回天了,志平就“哧哧”地笑,幸灾乐祸的。臭勇被志平笑得心里发毛,扭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志平竟理直气壮地迎着他的目光瞪过去,毫不示弱。法官都要来了,有法律护着,他不怕臭勇。
志平故意拉着长腔说,臭勇,法官要下来处理你打人的事啦,你可要做好准备抗住啊!
如此三番五次,臭勇忍不住了,猛地摔了棋子,骂,闭上你娘的臭嘴。
怎么?怕啦?志平的语调儿还是幸灾乐祸。
怕你奶奶个腿!老子这么严肃的一盘好棋被你搅成这样。臭勇骂着起身走人,起身的时候,还“砰”的一声憋出了一个响屁,引得周围的人放声大笑。
太阳落下去了,月亮升起来了。晚间扎啤摊又热热闹闹地练了起来,等春雷和志平喝完了最后一杯扎啤,也没见法官的人影。春雷拉了一把扎在领口的红领带,抱怨道,他妈的,闷了我一天的汗。
第二天,志平才想起给小李律师打电话,小李律师在电话里抱怨他,说今天法官要去,你怎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怎么没动静?春雷都来了,等了整一天。志平说。
那你怎么不来接法官哪?你不来车接,难道让法官打的或坐公共汽车去吗?他们都忙得很,要来接的。小李律师说。
我没有车,也不会开。志平说。那今天让春雷开车去接吧。
今天不行了,主管法官有别的安排了。等我再预约吧,约好后我再通知你。小李律师说。
法官来桑梓路调查取证时,秋天已经过去了,季节已经是冬季,树叶黄了,路边冬青的绿也不怎么清爽,有些灰土土的样子。可是那天日子却好,晴空万里,蓝天如洗,晴朗得让人感觉到不真实。法官看了看他们提供的发票,也看了现场,原告、被告做了笔录,还找了目击证人。
忙活了半天,春雷让志平安排去饭店,法官说不行不行,为百姓办事,不能这样。志平真心想请法官吃个饭的,不吃饭心里不塌实。就说为人民办事也得吃饭吧。最后还是小李律师打圆场,说现在要求得紧,大吃大喝就算了,就在家里吃顿便饭吧。
法官好说歹说还是同意了。春雷给志平使眼色,志平没明白,什么意思?春雷没办法,把他拖到门外,嘱咐道,在家吃什么?赶紧去饭店去要菜啊,像样点儿。志平领会,赶紧忙活去了。
晚饭很丰盛,吃饭时,法官的酒意喝上来了,三巡过后,法官有了醉意,扳着志平的肩膀说,兄弟,你的事包在我身上……趁这火候,春雷包了两个红包,悄悄地塞给法官。这次法官很正色地拒绝了,说,这事不行,让我丢饭碗吗?现在我们不敢,不,是不能了,政策知道吗?政策严酷了——放心,事会认真处理,小动作就算了。这一番话弄得春雷和志平还有些尴尬……
结果很快就有了,不到一个周,法院就通知当事人开庭。那天志平、春芽、春雷都去了,他们在小李律师的带领下,一帮人浩浩荡荡的挺威风。志平很意外,法官判案并不像电视上那样你来我往的舌枪唇剑,而是把他们叫在一起商量,不过在调解前,法官先严肃地谈话,进行了一番时事教育,说,作为国家公民要遵纪守法,要为国分忧,不能目光短浅,自私自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打打闹闹,酿成血案,并且双方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教训很深刻,要引以为戒,调解的结果是:医药费原告认百分之三十,被告认百分之七十,诉讼费各半,每人认二百五十元,被告臭勇加上诉讼费应付给志平七千二百五十元。双方签字。
这样的结果让志平和春雷都很意外,而臭勇在法官面前却唯唯诺诺的,爽快地签了字,微笑着离开了。
看着志平极不情愿的样子,法官就开导说,打官司就是明个理,出口气。这样的结果证明官司你们百分之百地赢了。臭勇光棍一根,也有难处,法律是教育人悔过自新的,你们街坊邻居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让他倾家荡产、脱一层皮,臭勇这样子,能不记恨?旧仇未去,又添新恨,这结世世代代都解不开了。所以,我们的判决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是合情合理的,况且也不全是臭勇一个人的错,一个骂,一个打,都是有错的。
志平像吃了只苍蝇,窝了一肚子火,又问小李律师。小李律师还是和蔼可亲的模样,他说,行了行了,就这样的结果,我也费了好大的力气。
判决书规定,臭勇必须在十五日内把七千二百五十元钱交给志平,但等了一天又一天,臭勇始终没有给钱。
桑梓路上的人都知道志平官司赢了,也知道臭勇并没有把应付的医药费和误工费给志平,双方闹了个半斤八两。志平找过臭勇两次,臭勇说过两天就给,但期限过了,臭勇依旧没有兑现。志平就去找法官,法官说,先缓一缓吧,我调查过臭勇的家庭情况,偿还能力确实有限,缓一时吧,十五天和一个月也没多大区别。志平根据小李律师的建议要求强制执行,没有钱他还有别的东西。法官说,就七千多块钱,能那么做吗?法律也有温情、人道,再想想别的办法,私下做做他的工作。
秋季到了冬季,冬季又到了春季。志平又多了一项新的工作,来回奔波在从桑梓路到法院的路上,有时还搭上春雷的小轿车。到了后来,法官也不耐煩了,指着堆积如山的桌面说,人民法院也不是给你一家开的,我们还要忙其他的案子,为其他的人民服务,之后就板起脸来不理睬了。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春芽的脾气却日渐恶劣起来,有时特意跑到王记玻璃店,指着志平骂,骂他软弱无能,不是血性汉子。她家务也不做,整日拉着个脸,志平的日子难过,度日如年。
转眼树叶黄了,秋风又紧了一层,树叶便全落光了,事竟一年多了。秋天像往年一样,一晃就过去了。街坊邻居见到志平就问,官司真的是打赢了吗?打赢了还解决不了吗?志平期期艾艾地说,赢了,真的赢了。而街坊邻居却在莫名其妙地笑。
春芽除了睡觉,一睁眼就是没完没了的谩骂;走在桑梓路上,志平碰到的也是一张张狐疑猜测的脸。
初冬的一个清晨,人们发现王记玻璃店的老板志平不割玻璃了,而是蹲在店里磨一把尖刀,磨得很仔细。春芽又到店里去找事儿,见志平磨刀,就看了一眼没有开嗓骂人。志平试了试刀锋,在衣袖上擦去水渍,放在袖筒里就沿着桑梓路往臭勇家走去,但是他的身子飘忽着,迟迟疑疑的,等目光里看到臭勇家的楼洞时,双腿就发软了,叹了口气,拐进另外一条胡同里。
第二天,志平又在磨刀,这次他把磨刀石搬在了门口,在大街上磨,邻居都围上来问,这是要干啥?杀人。志平恶狠狠地说。邻居捂着嘴微微笑了。围观的人多起来,志平磨得就更起劲了。磨一会儿试一下刀锋,再磨,再试……一直磨到了晌午,围观的邻居都不耐烦了,说,都削铁如泥了,还磨啥?不就是杀个人吗?老刀见肉三分快,不用磨了,赶快杀去吧。
在众人热切期望的目光里,志平站起身,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身后簇拥着一群大大小小的人。志平在前面走着,脊背上的汗就冒了出来,他走得很慢很慢,晃晃悠悠地,心在抖着,满手心的汗,几乎都握不住刀了!
臭勇家越来越近了,志平紧张得不能自持,他一时精神恍惚,身前身后是一个个踊跃的身影。终于到了臭勇家的楼下,志平的心扑通通地几乎要从嗓子里跳出来,胸脯大面积地起伏,他不知道如果这时候臭勇从楼上走下来,他能做什么?箭已在弦上,不能不发了,一群人都远远地站着,眼睛眨也不眨。就在人人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过路的邻居说,臭勇不在家,早上就坐车去啤酒街喝酒去了,志平的心轰的一声落回了原处,四肢瘫软,几乎摔倒,看的人都发出“嘘”声,说,臭勇这小子命大,躲过了这一劫。志平顿时来了勇气,他用刀尖指着窗户,臭勇,你狗日的出来,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傍晚,有邻居殷勤地打来电话,说看到臭勇回来了,醉得东倒西歪,正是解决他的好时机。志平不屑地说,我不和醉汉计较,让这小子多活一夜。接下来的几天,志平天天在楼下等臭勇,他也不进去,就蹲在楼洞口,手里的刀子不时挥舞着……也真是奇怪了,这臭勇竟几天都没有照面,也不知道在不在家。
直到几天后的早晨,臭勇才出来,看到志平,眯着眼睛伸伸脖子望了望,对眼前的阵式并没有惊慌,便点起烟抽着。一支烟快抽完了,对站在远处的人喊道,看什么?耍猴吗?人们哄然而散。臭勇竟没理志平,背起手向别处走去。
志平站着,手里的刀闪着寒光。臭勇没有丝毫畏惧,这大大出乎了志平的预料,也打乱了他的计划。难道臭勇看透了他的心思,其实磨刀扬言杀臭勇只是他的一个心理震慑,如果他怕死,怕他拼命,痛痛快快掏了医药费,就行了。
他真的能杀了臭勇吗?志平想想也不可能,他连只鸡都杀不了还能杀人?
事情雷声大,雨点小,回家遭到了春芽的数落,被逼急了,忍不住吼了一句,结果引来春芽更大的发泄,扑过来挠花了志平的脸。顶着道道血绺的脸面被赶出家门,没处可去,打电话喊来春雷,两人在扎啤摊上对饮起来。酒过三巡,志平诉着委屈,这事弄的,赔上一万多,唉!我不行,你也不行啊,桑梓路上的才人,还大学生呢!
春雷也郁闷,说,帐不能这么算,毕竟赢了官司。
志平借酒竟哭出声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春雷看着志平的样子眼圈也红了,长长地叹口气,说,我外教费回家没承认,也没上交,给你一万吧。
先……过去这事,等……我攒着再还你……志平抽泣着。
一天晚上,志平事先侦查了,确定臭勇在家,又给春芽电话,要加个班,晚些回去。然后确定没人注意他,才偷偷地钻进臭勇家的门洞,上楼去敲臭勇家的门。
“咚咚”。沉闷的声音在楼道里回响。谁?臭勇在屋里喊。
我。志平低声说。门开了一道缝,志平借机把一根香烟递进去,低声下气地说,兄弟,我进去有事和你商量。
臭勇开了门,退后一步,志平讨好地笑着,朝臭勇亮了亮空空的双手,进了屋,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纸包递给臭勇。臭勇大惑不解。志平说,兄弟,这是八千块,你在街坊邻居面前给我七千二百五十块,你给老哥一个面子,让我过了这道坎吧。
第二天一整天,没见到臭勇,志平失魂落魄……两天后,志平在小超市门前看到了臭勇,他盼望臭勇把钱给他,但又不能催,只好主动上前敬烟,远远地跟着他,心里胆怯,这臭勇不能赖吧,钱这么多,起了贪心不给他怎么办,那可真是哑巴吃黄连了,难道自己要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就在志平快要绝望时,臭勇将钱给了他。那是个秋日的午后,小超市前一帮邻居在闲聊,臭勇忽然间朝正往店里走的志平招手。志平快步走过来,臭勇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向众人扬了扬,然后塞进了志平的手里。
志平接着钱,手哆嗦着,身体颤抖着,竟然抽泣着抽泣着哭出声来。
这一幕给整条桑梓路的人留下了温馨美好的印象,都佩服志平单刀赴会,一身虎胆,硬是让臭勇服了输。
志平在桑梓路上腰杆挺起来了。志平,不是要为社区请电影吗?小超市老板对他喊。
请,我家春芽说,社区广场上多年不演戏了,让我回老家,请家乡的茂腔剧团来唱三天。志平说完挺起腰杆,叉起腰,沿着桑梓路从东走到西,又回过头来,从西走到东。
茂腔剧团如约来到了社区广场,整个桑梓路像过春节一样热闹,春芽坐在场地中央,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大气地说笑着,一口的海腥味。整整三天,志平家乡的茂腔戏场上,人們竟没有见到志平的身影,而每一场戏,臭勇都坐在前排,嘴里嗑着瓜子,身边放着扎啤,看得津津有味。
-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