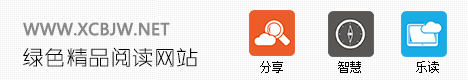一次去凤凰,拜望回乡的黄永玉先生。在他那座独得一城风光的夺翠楼里,先生聊及行踪,说他不在大陆与香港,便是待在意大利,在那里,有他三分之一的人生。欧洲之大,先生何以独宠意大利?那时我年轻脸皮薄,碍着面子,没敢开口问先生。这一疑问,却一直存在心里。
首赴意大利,是在1998年。从法国南部入境,第一站落在米兰,然后去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航机飞离罗马时,回望烟雨中的古老帝都,忽然意识到,从当代的时尚之都、近代的文艺之都,到古代的政治之都,我几乎是逆着时序走了一趟意大利。
前两年再去,先落罗马,接着是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又顺着时序将半岛再走了一遍。
去年,打算从西西里岛入境,由东南至西北纵贯意大利,可惜被别的商务行程冲掉了。这个想法,至今仍未打消。
差不多用了20年,几乎将欧洲走遍之后,我才慢慢悟出,黄永玉先生独宠意大利的理由。从古至今,但凡人类的欲望:美好的罪恶的,精神的物质的,群体的个人的,不朽的速亡的,都在这块土地上鲜花般绽放,绽放得自由自在,绽放得五光十色,绽放得如火如荼……在我眼里,意大利,就是一座盛开不败的欲望花园。

一
第一次站在米兰大教堂前,是一个夏日的傍晚。丛林般的尖塔,仿佛被灼热的晚霞熔化,随时都会熔岩一般流淌下来。教堂投在广场上的巨大阴影,如同一片燃烧过的纸烬,倘若有风吹来,便会扬得满城满天。
我想象,君士坦丁皇帝在这里颁布《米兰赦令》时,那万众欢腾的热烈场面,也该是这般炽可烁金。那是公元313年,一个石破天惊的年份!一位信奉多神教的东方统治者,颁令承认西方一神教的合法性,此种精神胸襟与胆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难有几个君王和元首可以望其项背。自此,基督教被认合法,被封罗马国教。这种开放主义的宗教精神,使米兰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教区,使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成了信仰自由的神圣象征。
当然,君士坦丁皇帝颁令的日子,这座被誉为大理石山的庞大教堂尚未建造。文艺复兴时代,是维斯孔蒂家族请来达·芬奇、布拉曼特等著名建筑师,筑造了这座规模仅次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的大教堂。达·芬奇为教堂绘制过无数设计手稿。在他的心中,这些呕心沥血的建筑图纸,应该比日后世人皆知的《蒙娜丽莎》重要许多。这种“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倒错,很难说不是一种历史的误读。被后世认为,画出了“人的微笑”的达-芬奇,还真是一位虔诚侍奉上帝的教徒。一定要封他为用艺术反叛宗教的斗士,至少在主观上有些牵强。文艺复兴的真正武器,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商人手中的金币。艺术,不过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战利品。
在米兰大教堂,真正炙手可热的盛事,应该是拿破仑皇帝的加冕。虽然米兰最早的居民,是公元前六百年迁来的高卢人,虽然十七世纪之后,米兰也曾被法国占领,然而,选择在这里加冕,还是显示了矮个子皇帝征服世界的勃勃野心。在一座并非传统领地的教堂加冕登基,接受四方朝贺,拿破仑皇帝那时的心情与欲望,应该也炽热到可以烁金熔岩。
二
踟躇米兰街头,古老房舍与街巷里,浸淫着一股浓浓的工匠气息。临街的门庭边,时常可见一两位头发蓬乱、围着皮裙的老头,坐在阳光里,执一根钢锥,一锥一线地上鞋底,或者持一把小锤,一锤一锤地给皮包钉铆钉。游客在一旁看久了,间或抬起头来,咧嘴笑一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埋头做手上的活计,不再与你搭讪。老人背后的门内,开有一个小小的皮具店,货品不多,一件算一件,皮质与五金配饰,上手一摸,便能觉出上佳的成色。款式不花哨,大体是传统欧洲和波希米亚风格两类。手工精致妥帖,一针一线匀称而细密。我买了一条老工匠刚刚做好还未摆上柜台的皮带,价格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块钱。那时用的不是欧元,是里拉,也没有懂中国话的店员。老头比画半天,后来等了翻译过来,才算最终搞定。
那条皮带,差不多扎了十年,出席过不少重大场合。如今有合适的衣裤,我仍会翻出来扎上。翻译说,意大利人率性散漫,唯独在手艺上一丝不苟。好些老头的背后,就是普通的住家,并没有铺面货架。你問他手上的东西卖不卖,老头摇摇头,继续埋头做活。翻译解释,这是给大品牌做的手工款,卖出去都是天价。
达·芬奇们没能把米兰打造成宗教之都,却种下了艺术和工艺的种子。这两样东西,在几百年的岁月里生长融合,让米兰成了时尚之都。在与巴黎的竞争中,米兰一直不输不让。总部设在米兰的奢侈品,有普拉达、范思哲、阿玛尼、华伦天奴、杰尼亚、杜嘉班纳、艾特罗等,加上总部设在附近的大品牌,阵容比巴黎强大许多。米兰每年春夏两季的时装周,是全球服饰、时尚界的盛会。说是时装周,前后会热闹一两个月。300多场各大品牌的时装秀,纵然跑断腿看花眼,还是会落下种种遗憾。下一个季节的面料、色彩、款式、工艺、情调和韵味,就在这里定格拍板,谁想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大体业内没人理会,市场也会无人响应。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型款,都是这里的设计师说了算。那些顶级的设计师,也只在米兰、巴黎两地流转,让他跑去别的城市,除非在这里找不到饭碗。
相比巴黎的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和迪奥,米兰的普拉达、范思哲、杜嘉班纳、阿玛尼等,更加富有当代艺术气质,时尚标记更分明,品牌活力更充盈,对非欧洲主流文化因素的吸纳也更大胆。一句话,米兰对文化风尚的变化更敏锐,对艺术风格的表达更舒放,对时尚引领的能力更自信。意大利人用物料和工艺,表达和满足人类时尚欲望的能力,几乎是一种天赋。米兰,则是他们展示这种天赋的首选秀场。
第二次去米兰,差不多逛了两天名品店。同行以为我血拼,不愿陪着进店门。两天下来,见我依然两手空空,便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困惑不解。其实,我逛名品店,只是为了去感受文化风尚和审美流变。绘画、音乐、影视、文学,没有哪个行当,比时装对审美心理和文化风尚的变化感受更准,响应更快。时装走哪一种风尚,其他行业要晚两三年才跟得上。对于出版,从内文到装帧,时装都是一个可靠的风向标。所谓畅销书,其实就是书业的时装。如何做常销书,跟着巴黎学;如何做畅销书,则要跟着米兰学。
一个时尚品牌历久不衰,无非三个要素:垄断核心资源,守护独门工艺,把握审美流变。说到核心资源,比方说面料,杰尼亚就是做面料起家的,虽然也供别人,最新最好的面料,却从来秘不示人。又比如,诺悠翩雅垄断了秘鲁的骆马毛,杰尼亚只能干瞪眼。骆马只有南美才有,其毛纤细柔软,保暖性能远超顶级羊绒,被誉为纤绒黄金。诺悠翩雅一件男装骆马毛短大衣,要卖人民币二十万元,杰尼亚望着垂涎欲滴。后来,发现哥伦比亚也有骆马,但被一家女装公司阿琉娜买断了。阿琉娜做的是顶级女装,因为贵得离谱,生意并不红火。杰尼亚思来想去,最后一咬牙,花大价钱买了阿琉娜,总算到手了骆马毛。杰尼亚立马推出了男装短大衣,售价比诺悠翩雅还贵六七万。以此比出版,便是版权和作家资源。谁家如果独自拥有了杰奎-罗琳,印书也不就像印钞票?中信这些年抢引进版权,其凶狠程度,如同杰尼亚抢骆马毛,也是咬牙顿足舍了血本。
2010年始,每年的全国书博会,我都有一场媒体见面会,比照米兰的时装发布,一来推出新书,二来发布文化风尚和审美心态的预测。媒体倒也关注,同业却无人响应,终究难成气候。一个行业,不能制造共同话题,不能引领消费风尚,其商业操作的能量,也就打了大大的折扣。
三
一到意大利,人们最急于抵达的城市,不是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而是威尼斯。那则“威尼斯每日都在下沉”的提示,让人觉得哪怕迟去一天,威尼斯都可能被海水吞没。到底是一座具有深厚商业传统的城市,这则旅游广告的奇妙与成功,大抵只稍逊于戴比尔斯的钻石营销。隔了十多年,再去威尼斯,我看到的海平面水线,仍在原来的刻度。
形似如意的意大利半岛,一条长柄远远地浮在海上,加上两座离岛,处处都是海湾、港口和濒海城市。威尼斯是一群困在大海中的小岛,密密麻麻地挤满房子,拜占庭、哥特和文艺复兴,各种风格相混相杂,远观玲珑奇妙如童话中的王国,近看则恍若隔世,难辨醒里梦里。由于海水浸漫,大多的建筑像是升白海底。清波荡漾,建筑与倒影融为一体,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可能倾倒在海中。海水仿佛在缓缓上升,感觉用不了多久,便会没上屋顶,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底王国。只要身处威尼斯,心中便扔不掉这份担心。这种若有若无的幻灭感,使威尼斯美得让人怜惜,美得叫人揪心。如同一个病弱的美女子,不仅让人倾慕其美丽,而且让人担忧其不测。
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可不是这副病弱女子的模样。那时节,威尼斯商人满欧洲奔跑,远的跑到了非洲和亚洲。车载船运把赚得的金币银圆拉回来,将这群小岛堆垒成了欧洲重要金融中心。西方学者形容威尼斯兴起的过程:“从一个泥泞的礁湖崛起为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宛如令人观止的海市蜃楼,从水中呼啸而起。”当然,有钱的日子难免挥金如土,岛上现存的那些华丽建筑,不是在那时兴建的,便是在那时扩建的。华贵的大理石和华丽的彩色玻璃,将各种用途的建筑,都装饰得宫殿教堂一般。用炫富挑战教会,用财富争取人权,这便是威尼斯人的文艺复兴。富有让威尼斯人过了好日子,却背了坏名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为富有的威尼斯商人,画了一幅比历史更让人信服的漫画,将人类对财富的欲望,做了一次史诗般的定格。
没钱的人关注钱怎么花,有钱的人关注钱怎么来。这事看上去很荒唐,细想道理却很明白:在任何一个时代,财富关注点的差异,都会衍变为道德立场的对抗。在人类的历史上,欲望每每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其结果,道德赢了当时,金钱赢了未来。
四
无论以地形还是历史作喻,佛罗伦萨,都是意大利光彩夺目的一枚胸花。
在好些艺术家眼中,意大利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就是梅迪契家族。这个简单的等式,未必吻合历史学家的判断,然而,只要你漫步在佛罗伦萨的街区,无论拜谒华丽庄敬的教堂,群星璀璨的美术馆,还是闲逛古旧斑驳、花草掩映的街巷,你都会沉浸于一种深不见底的艺术氛围,都会迷失于无所不在的梅迪契家族故事……
其中的一则故事,充满传奇也极具象征意味。1492年4月5日,圣母玛利亚教堂正在晨祷,一位妇女突然跳起来,发疯似的奔跑,大叫大嚷,说她看见了一头角上喷火的公牛,正疯狂地撞击大教堂。紧接着,人们听到一声惊雷,大教堂的穹顶被雷电击落,屋顶上作为梅迪契家族象征的镀金球咣当坠地。三天后,洛伦佐·德-梅迪契溘然辞世。洛伦佐一死,被其供养的大批艺术门客作鸟兽散去,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即告结束。
站在教堂的大厅,仰望那颗后来被安装复原的镀金球,回味那个具有天谴意味的故事,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个创造了佛罗伦萨历史辉煌的梅迪契家族,如何评价推动文艺复兴达至顶峰的洛伦佐这位无冕之王。
梅迪契家族的祖先,大抵是一位藥匠或医生,因做药或治病发迹,之后扩张至羊毛加工和金融业。开办的梅迪契银行,是当时欧洲最具规模、最富声望的银行之一。家族由银行家而至政治家、教士,并获得贵族身份。梅氏一门先后产生了三位教皇,多名佛罗伦萨统治者,一位托斯卡拉大公和两位法兰西皇后。由一介寒门,终至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上流社会中心。这一传奇的背后,隐匿着商人阶层在与教会、皇室的博弈中,日渐走强的历史趋势。世俗社会的崛起,依托的是人性的觉醒和人欲的膨胀。继教皇的权杖,皇室的冠冕之后,金钱成为第三种权力象征,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隔海相望的西班牙皇室,其时还在为最终驱逐摩尔人浴血奋战,为追缴税收将犹太人赶得鸡飞狗跳。而梅迪契家族,则靠着银行和贸易,将佛罗伦萨治理得市井繁荣、艺术鼎盛。一大群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家,在梅迪契家族的荫庇下潜心创作,推出了一大批彪炳古今的作品。达·芬奇师徒,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艺术家。
五
假如没有梅迪契家族,意大利会有文艺复兴吗?或许会在米兰、威尼斯、罗马、西西里兴起?历史自然是没有假设的,我们只能从历史事件本身,去找寻必然如此的证据。面对乌菲齐博物馆里的那些藏品,我想到了洛伦佐。想象他在专为供养的艺术家修建的花园里,怎样年复一年地同艺术家讨论这些作品。是什么驱使他供养那么多的艺术门客,而不是像春秋时代的士子豢养谋士,像江户时代的幕府豢养武士?是他作为一位杰出诗人的艺术情怀?是他作为一位卓越鉴赏家的艺术品位,还是他作为一位统治者的艺术占有欲?或许兼而有之吧。当然,也可能都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世俗的意义上,洛伦佐其实还有更紧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他更需要为自己谋取一个名正言顺的政治或者宗教身份。在共和体制的佛罗伦萨,作为统治者梅氏家族的代表,洛伦佐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公民。洛伦佐自己也承认:“我不是佛罗伦萨的君王,我只是一名享有一定权势的公民。”其时周边的许多地方,早已经是君主体制。以梅氏家族的财富与权势,谋求改旗易帜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可是洛伦佐连尝试都不曾做过。或许,他比谁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佛罗伦萨共和传统的坚如磐石;或许,他根本就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历史的罪人。
当然,洛伦佐并不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在处置政敌时,也使用过血腥的手段。但在权力安全与心灵安妥的终极选择上,洛伦佐选择了后者。“浸染着贪婪,而又充满着惊人期望的一颗心呵,如何才能找到安宁?”这是洛伦佐自己的一句诗,应该可以视为他灵魂的自我追问。洛伦佐把精力和金钱投向了宗教和艺术,让人性自由烂漫地开放出一个灿烂的时代,并由此博得了一个历史的好名声。
艺术家应该供养,还是放养?这话题我们争吵了几十年,外国人也跟着起哄了几十年。其实“困厄出文豪、愤怒出诗人”,与“穷养工匠富养艺术”,从来都不曾放之四海而皆准,每每在同一个国度,同一个时代,既有在困厄中崛起的艺术家,也有富养中诞生的艺术家。梅迪契家族的供养,更本质的意义,是给了艺术家自由创作的社会环境,经济支助的意义远小于精神庇护的意义。梅氏家族供养的艺术家,即使思想出轨、艺术出格,也不会招致社会的迫害,这才是文艺得以在佛罗伦萨复兴的内在因由。达·芬奇的学生,梅氏供养的艺术家、建筑家瓦萨里,在其美术史著作《艺园名人传》中,首提“文艺复兴”概念,他所指的复兴,不外乎是在题材上由一神教向多神教回归,在主题上由神性向人性回归。人性的自由与人欲的舒张,在艺术上获得了梅氏家族默许的合法性。历史的轮回,就是这般大大咧咧到令人无语:从《米兰赦令》在宗教上解禁一神教,到佛罗伦萨人在文艺上回归多神教,这两次方向背反,目的却一致的人性解放,前后耗去了一千年。
六
虎倒雄风在。罗马,就是这样一座余威犹存的帝都。
二千多年岁月的冲刷,罗马作为欧洲政治中心的威严与气势,依旧真切可感。一个城市,见没见过场合,经没经过大事,你往那儿一站,自然会有一种气场。市民淡定的眼神,从容的语速,还有举手投足间似有似无的仪式感,都会告诉你,这座城市见识过怎样的阵仗,演绎过怎样的壮举。至于那些无所不在的历史遗存,虽然颓圮败落,虽然荒草残阳,却都是无字之碑文、无声之史诗,随时都会往你心里钻,让你绕不开躲不掉。在罗马,只要一闭上眼睛,你就能听到元老院里华丽而冗长的论辩,就能看到罗马军团的无数战舰,箭一般射向天水苍茫的地中海……
我到大斗兽场,是在早晨六七点钟。游客通道尚未打开,周边也没有什么行人。起这一个大早,是想独自一人安静地面对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时代,是期望孤独静寂中,听听那殊死搏杀、绝命嘶吼的历史回响。清晨的阳光,洁净得炽白透亮,照耀在黝黑的拱门和石墙上,冷冷地泛着青光。石头上的水滴,说不清是暗夜的渗水、晨早的露珠,还是历史遗落的斑斑泪点,以手轻触,一股沁凉直透心底。是因为在历史的血泪里浸泡太久吗?炎炎夏日,仍如此寒彻筋骨?拱门远处的墙基下,枝枝权权地长着一团野花,碧绿的圆叶,复瓣深红的花朵,形若玫瑰,颜色却更为裱丽。厚实高大的石墙,竟没能遮挡住花朵的阳光。没心没肺的野花,兴高采烈地开在阳光里,兀自得意地斗彩秀艳。或许因历史已凝为石墙,这艳若夭桃的花朵,反倒透露出一派生机,引人生出生命不绝、历史不竭一类的联想。
大斗兽场的原名,是佛莱文圆形剧场,建造于公元前一百年的样子。究其初衷,大抵是效仿古希腊人用来演戏。只是规模更大,比我在雅典卫城外看到的大剧场,宏伟气派了許多。剧场上演悲剧,在古希腊,那是举国的盛事,每每万人空巷。罗马人垒造的这个剧场,容得下四五万人,倒也显示了罗马不让雅典的雄心。依此也可推测,当年罗马的城市,已快速膨胀,市民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里应该是上演过戏剧的,只是罗马人的戏剧,不若希腊人的扣人心弦。至少留下来的剧本,不可与希腊媲美。或许,这也是后来将剧场改作斗兽场的一个原因。斗兽场最早是斗狮,那是一种执行死刑的方式。市民被招来观看斗狮,如同国人被唤看斩或枪决人犯,应该是杀一儆百的意思。因为人犯倘若杀死了狮子,便可获释自由,这便有了悬念,有了情节,有了看头。于是象征性的悲剧,便演绎成了血淋淋的悲剧。决斗者的命运,就悬在那刀来剑去的一瞬之间。后来有了职业的角斗士,大多是买来的奴隶或俘虏的兵士,为了自由的身份,他们要用性命去表演。这样壮烈的活剧,用淋漓的鲜血,将人性毁灭给人看,看着自然更加激动人心。可惜和可恨的是,它所唤醒的,不是人类的同情心,而是嗜血嗜杀的动物本能。这是意大利人绽放的一朵艳丽而恶毒的欲望之花,譬如罂粟,恐怖而充满诱惑。
前些年,HB0电视网拍了部大尺度的电视剧《血与沙》,写的就是古罗马角斗士。导演企图逼真还原古罗马的荒淫和凶残,性与厮杀,完全没有躲闪遮蔽。那是真正的酒池肉林!真正的荒淫暴戾!当我走进斗兽场,那些人物:元老与执政官,贵族与美妇,市民与角斗士,一一在场中归位。一声厮杀怒吼,一片振臂欢呼。那吼声一声比一声惨烈,那欢呼一阵比一阵狂热,逼着我双手掩耳,匆匆逃离了斗兽场。
七
元老会堂,是我两次都惦记着要去的地方。
大约公元前五百年,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共和国。比起希腊的城邦共和,罗马早了一百年。是罗马人为后来人类的政治体制,创造了一种文明的模型。
罗马广场的东面,便是元老们当年议事的会堂。那时应该是一栋庞大的建筑,包括了好几个会堂。毕竟历时太久,只剩了断壁残垣。有一个会堂修复了屋顶,据此想象,大体可以复原当年的形貌。夕照之下,那些倾卧在荒草中的石柱与石块,又各自运动起来,快速地回归到原初的位置,还原为当年庞大巍峨的建筑。身着长袍的元老们,气宇轩昂地进进出出,在宽敞华丽的大厅里侃侃而谈,将土地、物产、税赋、奴隶的种种纷争,由战场迁到了会堂。各个利益集团由真刀真枪的厮杀,变为了唇枪舌剑的论辩。那是一次多么迷人的迁移,多么伟大的改变!唇舌终于替代了刀枪,妥协终于替代了任性,共识终于替代了独裁!
整整五百年。那是人类还没有进入公元纪年时代的五百年!很可惜,元老们用五百年的时间,也没有将这个文明的制度筑牢固稳,最终让这个制度如同这座会堂,坍塌在荒草斜阳里。
渥大维创立了罗马帝国,重新披上铠甲,拿起刀枪,坐上了专权独裁的皇帝宝座。他用刀剑杀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也杀死了一个民主政体。等到意大利人回头复兴这套体制,差不多已是两千年后(极个别的城邦除外)。也有人说,议会制度的最早萌芽,是在冰岛的一个山洞边。即使如此,那也只是转瞬即逝的灵光一现,完全没有政治实践的历史价值。
-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