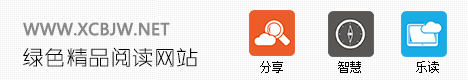我看到有的人,馒头咬了一口掉地上就不要了,苹果因为长得不好看就扔了,一条鱼没吃几口就当做剩菜倒了,我就想起了我们当年在饥饿中煎熬的情形历历在目……
由于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而1960年是三年中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当时我们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耕种土地。1959年,我们没有从生产队分到粮食,只分了点红薯和白薯干,自然不够吃,于是我们把棉花籽、红薯蔓、玉米芯用碾子碾碎,掺上红薯面蒸成窝窝面,配上瓜菜,就这样熬过了这年冬天。
1960年春天,饥饿更甚,一点红薯干也吃完了,人們开始扒树皮,扒得最多的是榆树,榆树皮无味且有粘性,扒下来晒干,用碾子碾成面,能和别的东西粘合在一起拍成饼子。

等树木都发了芽,野菜也长出来了,人们好像有了期盼:榆钱、榆树叶好吃但有限,还没长好,就有多少人等着采它。椿树分为香椿、菜椿和臭椿,香椿自不必说,菜椿也很好,无味,人们争相采摘,就是臭椿也有人吃。洋槐花是美味,做菜、做汤都可以,槐树叶、杨树叶也在采摘之列。现在嚼一下很苦,但在当时,洗净、煮熟味道还不错。野菜能吃的种类也不少,像扫帚苗、沙朋、杏仁菜……只是不等长大就被无数双眼睛盯上。
当时我在魏庄上高小(相当于现在小学五六年级),距家三里地,放学回家不走大道,而是绕到地里看看有没有可挖的野菜。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个生产队种的菠菜收割了,地里留有菠菜根,我发现后如获至宝,挖了一书包,到家煮熟吃起来像点心。因此,直到现在我也爱吃菠菜根,吃起来甜甜的。
星期天我会拿一个布袋到远一点的地方采树叶或者草籽。那年暑假,我采的树叶和草籽晒干竟然装了满满一瓮。
记得我有一个梨舍不得吃,结果时间一长烂了,很是可惜。母亲却说:“有烂梨,没烂味,能吃。”我和母亲一人一半吃了。说来也怪,我们当时吃这些东西也不闹肚子,只是有的人因长期吃不到粮食,全身浮肿。
高小毕业后我考入隆尧一中,经济形势仍然严峻。我们到校的第一节课是到地里捡菜叶。捡回来后,厨房的工友将其洗净、切碎,就是我们的菜。主食是高粱面饼子或煮红薯干。这样维持了半年。
到第二学期再开学,我们就改为一天两顿饭:上午九点吃饭,下午五点吃饭。据说学生的口粮是每人每月十二斤,没法正常开饭。
我们宿舍还发生了一起偷吃事件:一位同学从食堂领的花籽仁(棉花籽去掉硬皮)掺了面粉的黑馒头,没吃完放到宿舍就上课去了。另一位同学因病在宿舍休息,可能实在是太饿,身体又不舒服,就把馒头吃了,遭到全宿舍人的批评。其实这位同学的品行非常好,可见她当时饿昏了头。
我有一次早晨起来上厕所,站立起来时,眼前一黑栽倒在厕所里。就这样一天两顿饭维持到暑假,暑假过后再开学,也就是初中的第二个学年,我们就被通知就近上学,我被分到了我们公社(乡)的未庄中学。
我们村的北面是一片沙滩地,生产队不种庄稼,栽满了树。有人就在树的间隙除去杂草,下雨后种上绿豆、谷子等杂粮。我们也开了一片种了绿豆,那年有雨,我们收了些绿豆。后来生产队干脆把那些不种的荒地给大家分了,我们种了高粱、谷子和绿豆,母亲还在生产队种不到的边角地栽了红薯。那一年收入颇丰,家里堆满了高粱穗、谷穗、豆荚和红薯。母亲每天忙着翻晒和脱粒。
从此我和母亲不再挨饿。
在未庄中学上了一年,经济形式逐渐好转,初中的第三个学年,我又被要回隆尧一中,从此开始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