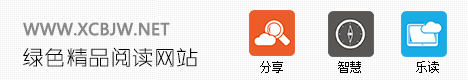谨以此篇,纪念一个早已远去的朋友。原谅我是一个习惯旁观而又无可奈何的人。
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说,鼻梁隆起的人多半是极为固执的。
最初和她熟络起来是因为我们一起在一个食堂吃饭, 是在那个下午,她站在耀眼的光中,叫出了我的名字。那时候她真的是个自信开朗的姑娘, 对朋友很仗义,
像是大姐姐一样, 好像没有她解决不了的事情。 她和班里男生的关系处得也极好, 课下一起打球占场,并不扭捏。我一直觉得,没有人该讨厌这样一个姑娘, 她这样好,
她是怎样都好的。
就因为这样,听到有人说她不好,我还是很诧异的。 “你不觉得她特别装吗?和男生处成这样。” 话是一个极为漂亮的女生说的,
许是自命不凡的性格让她见不得有人比她的人缘好上不少吧。可我是很少直接发表这样观点的, 我只是笑了笑, 没再说话。我想,
这种话题,进行下去又有什么好处,若是不接话,大概这件事也就会渐渐被人忘却吧。可不久我就发现我错了, 有人看山是山,
但也有人看山是乱石,认为过分碍眼。而其实乃至现在,我也想不通,面对讨厌的人和讨厌自己的人,到底是该选择无视呢还是努力融洽。
我曾听过一种有趣的说法,说年少时的倔强,是对整个世界的骄傲。她便是带着这种骄傲,仿佛站在了许多人的对面。在此之后,她的玻璃杯不知摔碎了多少,但从没有换成别的材质。
“换了不怕摔的,不就是我怕了?”
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说话的感觉有些大义凛然。那个样子令我险些笑出声,是不是只有如此率性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率性的话。那时候我甚至想将她的生活比作最美的丙烯画,拥有最亮眼的颜色,而她本人就是画作的主人,画上每一笔都由自己肆意创作。
可是无论多么缤纷夺目的生命都会畏惧狂风肆虐。那天窗外充满了泥土湿润的气息,没多久就是乌云密布,可忽然闪过的闪电让我看清了她脸上未干的泪痕。她被人告发在校外早恋,学校各级干部轮番警告谈话,把她的父亲奶奶请了个遍。“没妈管教的孩子就是不知道羞耻。”
这话难听得很,但没有人出来制止,我也没有。
接到她哭诉电话是在那个暴雨的晚上,
她断断续续的哭声和窗外敲击不停的雨一起砸在我的耳边,那天真的灰暗极了。那天她说了许多,说了她从不参加家长会的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说了那些从不了解事实就不断说她坏话的同学…后来挂断电话前她却笑了,笑到令我毛骨悚然。她说,不想为人鱼肉,她说要我们都远离她,反正没有人愿意和讨厌的人和坏学生为伍。我一时接不上话,愣神间便只有挂断的嘟嘟声不绝传来。我确实什么都没法为她做,
也可能她觉得说没有做更合适。我觉得我从未了解过她。我不知道她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但一定不是我这样。我也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被这样多人讨厌,谁也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理由吧。
我只隐约感觉到她也许并不坚强,她也许是一个把自己装在铠甲里的小姑娘。恍然间有些哽咽,想为自己的旁观流泪。
再之后她就不与任何人亲近些了,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特别是英语。很难有人做事能没有丝毫成见不贴任何标签,
比如我在这里这样说我们曾经的英语老师是那种从来只关心成绩好的好孩子的人,
也比如在一次英语课上对着早已被贴了成绩垫底标签的她大发雷霆的英语老师。从早恋到顶撞老师、不团结同学,英语老师一一细数,最后扣上了家教不严、性格扭曲这种大帽子。班里同学早已领教过她愤怒时的怒火,英语老师却是第一次见识。当她把杯子书本一律砸到地上的时候,老师毫无疑问地把她推出了班门。她在班外撕心裂肺吵了许久,之后被教导主任带走,她选择休学,说这样的生活不过也罢,再之后直到从那所学校毕业直至现在,
我都没再见过她了。听说她去了很远的地方,有着和同龄人并不相似的生活,早已做不回常规人眼中的好女孩。也许她会说没有必要吧,但她怎么会不在乎呢,她是很在乎的吧。不然又为什么要对那些别人贴在她身上的标签反应这样激烈。我们没有人愿意接受别人为自己贴上他们眼中自己的标签,她也是,可是她和我们大多数人又不一样。也许是没有人愿意和她一样。
你有体会过那种亲眼见到一个人走向末路的经历吗,那种束手无策的无力感。我们对那些思想陈旧的人嗤之以鼻,但是又对这些首先与我们与众不同的人报以异样眼光。我们做惯了旁观者,再也不愿意站出来说什么与众不同的话。但也许这都算不上错,我们很多的人只是选择了一种,最普通最能不成为异类的生活方式吧。可是,在这一生中,我们是不是都会遇到,像这样骄傲而又倔强的女孩,像这样逐渐面目全非的时光。
间珠琉璃锁长怀,往事一回首,再不成憶,苦成章。
-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