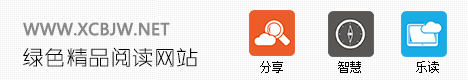欢迎来到小窗笔记网!
临近年关,少不了的就是参加酒席,每逢这时,母亲总爱念叨:“人情债难还,你家二叔的儿子乔迁了,对了,邻居家的女儿好像要下个礼拜出嫁。”同时还不忘在本子上记下要花费的礼金。
赣南地区把吃酒席习惯叫作“吃酒”或“吃东道”,从我对吃酒有记忆开始,母亲就一直反复念叨着吃酒席要花费大量礼金,十几年没有变过,而说到底,对吃酒心境改变的只有我。
幼年时家里拮据,在村子里居住,母亲伺弄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所以素日里主要以母亲栽种的青菜萝卜为食,猪肉是家里难得的菜品,然而这肉多被母亲用来熬汤,为全家人清火。有时,母亲将熬过汤后的瘦肉再用来与白菜萝卜一起炒,但这肉早就失去了味道,难以下咽,煮过汤后再炒的瘦肉还老塞牙缝,这便愈加让我对吃酒充满期待。酒桌上有我过年甚至是过年也吃不到的荤食,哪怕是现在再普通不过的甲鱼、虾一类的生鲜。
四、五岁左右的时候,我还能和母亲一起去吃酒,我想无非是我年纪小,放在家里无人照看,母亲又是一个极怕欠人情的人,不愿意把我交给邻居照看,外加当时食量小,不会占酒席上同桌人什么便宜——毕竟她出的只是一个人的份子钱。
等我再大一点儿,她就不愿意再带我去,怕被人说闲话。老家那边的风俗,父母带着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去吃酒,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但那时垂涎酒席上美味的我,听到她说要去吃酒前,总会赖上几天,母亲觉得带我这么大的人去吃酒席占了别人便宜,不管我怎么闹,她也不肯。她是个严厉的女人,耐心被我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扬起手,做出要打我屁股的姿势。我也是个“没骨气”的,见到母亲这般生气,只能抽噎着说道:“我不再赖着你了。”

2
十二、三岁左右,母亲将那个代表全家吃酒席的人换成了我,这个时候,家庭经济条件好了许多,能在酒桌上吃到肉类对我的吸引力不再那么大,这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从饭菜变成了我的表姐。因为我们两家住得近,亲戚朋友也差不多都是相同的那些人,遇到吃酒,两家人一般都要去同一家,因此母亲就让我与她一块儿去。
做东道的主人往往会开辟出一两桌,专门招待小孩子,没有大人们的束缚,自然没那么多规矩。不管一桌十人是否到齐,总会有一两个胆大的孩子提前将果汁、可乐打开,先一饮为快。开过头后,我与表姐也加入这个行列。大人们不在这一桌,少了唠叨的声音,因此我们也早忘了来之前他们的叮嘱,偷偷喝上小半碗啤酒。我发现自己并不能像父亲那样畅饮,啤酒没有我想象得那样好喝,喝完后只觉得满口涩味。最愉快的莫过于抢菜那一刻,一碗精致的五花肉刚端上来,立刻会惨遭几双筷子的“摧残”。表姐主动承担起照顾我的义务,挑出瘦肉夹给我,然后再去满足自己的味蕾。五花肉的瘦肉已经被抢光,剩下的肥肉早已糜烂得不成样子,她只好等着下一碗菜品。
当然,我与表姐在一起吃酒的这些年中,也不仅仅是和年纪相仿的人坐在一起,有时专属于小孩子的酒桌满人后,我们只有插到有空余位置的席上,规矩也自然多起来。比如饮料瓜子要等十个人到齐后才可以开启,更别说想要体会抢菜那一刻的欢乐。更加不幸的是,如果遇到一些计较的妇人,她们甚至会把每碗菜分成十等份,精明地记下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我现在还清醒地记得在一次酒席上,我与表姐吃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卤味鸭翅,奈何那又咸又辣的味道在口中消散不去,只觉得一只吃得不过瘾,想要再来一只。我与她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盘盛着鸭翅的碟子,心照不宣的我们趁其他人不注意时,将“魔爪”同时伸向盘中,得逞后生怕别人发现我们干的事情,只能囫囵吞咽,来不及细细品味,残留在口中的味道也没有之前那只来得浓,倒是忐忑不安,生怕那些妇人发现我们偷吃别人的份,在席上不停地碎碎念。那顿酒席因为“偷吃”的这一只鸭翅,害的我们俩剩下的时间里只得老老实实,尽量让她们忽视我们的存在,而我对接下来呈上的菜品也食之无味,我想表姐应该同我一样,担心被别人发现干了“坏事”而无心继续吃下去。
酒席快结束时,还没有听到有人念叨属于自己那份鸭翅少了,正当我们怀着暗自窃喜的心情准备离开时,拾掇菜品回家的妇人中先是有一人发出惊呼:“哎呀,我那份鸭翅怎么没了?”我内心一跳,侧着脸看向表姐,转动眼珠,发出“怎么办”的讯号。她也眼珠转动,然后一瞪,传达着叫我不要声张的话语。紧接着,又一妇人马上望了望盛着鸭翅的盘子,发现它空空如也,也说自己那份没了,还补充一句:“我记得我明明没吃呀!”于是有人接嘴:“会不会是有人多吃了?”席上静默,某些人赶着离场,说了圆场话:“可能是帮工数错了,毕竟那么多桌要准备,一时没数准十个呢。”有人应和:“是呢,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两个妇人虽然面色依旧不善,只能自认倒霉没有及时吃,否则就不会少了自己的那份,心中不快,只得碎念:“怎么有这样子的帮工哦。”
我与表姐趁着此刻飞奔而走,生怕她们发现是我们干的。直到跑到离酒席很远的地方方才停下来,抚摸着刚刚剧烈奔跑后产生痛感的肚子,相视着哈哈大笑。
3
十五六岁的时候搬家去了县城,县城人家办酒席大多是承包在酒店里面,不像乡下,要自家承办,也不需要像村中一样,主人提前两天请好主厨和帮工,买好酒桌上的各种材料。县城的宴席都是由酒店一手承包,主人无需多准备材料,客人们基本上是快到宴席开始前写好礼金,直接坐上酒桌,无需等待多久,宴席的菜品就会摆上桌子。
村中办酒席比这个讲究多了。打过炮仗后开始写礼金,从上午开始,来的人陆陆续续持续到酒席开宴,大部分人是写完礼金先回家。酒席快开始前,有专门的帮工拿着誊抄礼金簿的名单,在村中告知我们,可以开始去主人家吃酒了。母亲会早早写好礼金,而我则在家,等待着被叫去吃酒,等待被叫的这种心情是在县城吃酒体会不到的。
縣城吃酒,表姐自然没有陪在我的身边,上桌之后的开吃,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焦急地等待着下一碟菜呈上来,我也渐渐成为他们的话题中心。如果和亲戚们一桌,每次询问成绩是必不可少的,我只能在心中默哀我那惨不忍睹的成绩后,违心回应他们“还好还好”。不熟的人也要来问几句:“妮子,你是不是快高考了,成绩怎样啊?想考哪个大学呢?”我打着哈哈:“这个呀,成绩还好,本科应该可以吧。”有时坐到在大门口旁边的座位,可以字字句句地听到宾客的奉承和主人不断地应和。不约而同地说着“发大财”的宾客们与满脸堆着笑回答“一定一定,你也是”的不厌其烦的主人,彼此敬完酒后,表情再度恢复到严肃的模样。
大厅内围坐在一起的妇人,此刻比在菜市站立着指指点点砍价时更有气势,她们讨论着主人家新装修的房子亦或是美丽的儿媳,同时磕巴着瓜子的尖细声突兀喧闹,那几桌聚在一起的大老爷们儿互相敬酒吆喝,推推搡搡中你敬我酒,我给你再添点,大大小小的瓶盖铺满桌面。几岁大的小孩子站立在凳子上,指着对面的菜品嚷嚷道:“妈妈,妈妈,我要那个!”母亲赶紧抓住孩子继续往前倾的身体,在他耳旁说着话:“小心点儿哦,你要什么,妈妈夹给你。”一边说,一边还不忘用纸巾抹去孩子嘴角的食物碎屑,孩子只能规矩地坐在凳子上,露出一个头,满脸不情愿地等着母亲夹过来的美食。酒席上的菜品,赣南人必备的鱼丸和肉丸,此刻吃起来还不如小摊贩上的小肉丸拌辣椒来得可口。偶尔有新菜品,吃那十人份中的一份,少得可怜,也不过瘾。
而我就在嬉闹声、祝福声、劝酒声和酒杯瓶子的敲击声中,等待着酒席的散场。有时,我故意忘记父母的嘱咐,在席上偶尔喝上一两口。酒量极差的我,喝着八度还兑了雪碧的红酒,也会立刻变得满脸通红,晕乎乎地睁着微眯的双眼,看着一双双在桌面上夹菜、干杯、倒酒的手。一想到这就是我以后的样子,惊恐之余,只得和旁边的人絮絮叨叨地讲话,试图将这种可怕的感觉抛之脑后。
容不得我细想,端菜忙不过来的服务员提醒我把她手中的某碗菜盛上桌面,我小心翼翼地将微烫的瓷碟端起,在桌面上寻找空余位置放下,这个过程中,我惊恐地发现我由那个曾经在凳子上看着大人们放下菜品的孩子,已经变成了那个放菜的人了。
-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