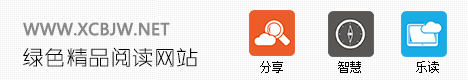艾克斯是最能代表普罗旺斯地区特色的小镇,在其边缘矗立着1000多米高的圣维克多山,与红瓦屋顶的村庄、蜿蜒的溪流、茂盛的松林以及广阔的葡萄园,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漫步在艾克斯的镇里镇外,我对圣维克多山若隐若现的锯齿状山峰总是百看不厌——当我在乡村咖啡馆啜饮一杯浓咖啡时,当我在芳香四溢的步行道上徜徉时,当我在从不同视角欣赏它的色彩变幻时。一次,我入住由18世纪农庄改建而成的乐比格内酒店,透过客房窗户,我甚至看到了山峰发出淡淡的光芒,仿佛定格在画框中。
人们大都以为,圣维克多山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发生在山脚下的一场古代战争。确实,公元前102年,罗马人就是在这里战胜了野蛮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建立了第一个远离帝国的军事要塞。据说,从此以后,这座山被命名为圣维克多山,以纪念那场胜利(Mont
Ste-Victoire,英语为Mount Saint Victory。victory是胜利的意思,saint则是中世纪基督教徒加上去的)。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由于钟灵毓秀的艾克斯诞生了艺术天才保罗·塞尚,这座恢宏壮丽的高山得以在这颗星球上焕发出更多光彩。

出生于1839年的塞尚自幼对圣维克多山情有独钟。“还是孩提时代,他就时常和埃米尔·左拉、让-巴蒂斯坦·巴耶等小伙伴一起,在山麓的原野上奔跑、攀爬、狩猎,目睹并感受着圣维克多山的四季变化。”塞尚的曾孙、业已退休的现代艺术专家菲利普·塞尚说。
塞尚曾离开故乡去巴黎求学,在那里他和卡米耶·毕沙罗、爱德华·马奈、克劳德·莫奈以及皮耶-奥古斯特·雷诺阿等画家相交甚深。受毕沙罗的影响,他在色彩方面不断探索,越来越像一位印象派画家,颜色暗淡低沉、笔触支离破碎的《自缢者之家》(The
House of the Hanged Man,
Auvers-surOise,1873)就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尽管如此,在这幅画中,你仍能看到他是如何大胆打破一成不变的艺术规则,如把前景和深景模糊化,透视故意不准确(一条小路通向左方;一条河岸以看似别扭的角度向右方倾斜)。
塞尚的作品并不都为当时的批评家接受,而心怀一颗乡村男孩赤子之心的塞尚,也意识到自己不属于巴黎;他属于故乡普罗旺斯。尽管他有时也住在马赛附近的埃斯塔克、瑞士和巴黎,但艾克斯始终珍藏在他的灵魂深处,圣维克多山也渐渐成为他最钟情的创作主题。
“一开始,塞尚在自家亚得布番农庄的庭院里,从远处来画圣维克多山。”菲利普说。而到了晚年,塞尚有意识地对圣维克多山给予了更多关注。他用更细致的笔触和更丰富的色彩,从各个角度来描绘圣维克多山。
为什么他会如此痴迷圣维克多山呢?
“画家对这座自然灯塔的质地(地质学)和结构(建筑学)充满热情,”菲利普解释道,“他目睹了圣维克多山每个季节、每个时刻的变化,他对此了然于胸。”
塞尚决定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像画建筑物一样,来描绘出圣维克多山的磅礴气势和恒久伟岸。当然,他在其他主题的作品中也运用了这种技法,包括静物画和不朽的《浴者》(Bathers)系列。但这些与他最钟爱的圣维克多山系列作品还是不能相提并论。从1870年开始,塞尚一共87次把圣维克多山搬到画布上。而随着他画得越多,他的画风越来越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因为他把画面提炼到色彩的几何图形。“老实说,如果要我虚构或想象细节,我宁愿捣碎画布。”他曾告诉朋友,同时也是作家和艺术批评家的乔奎因·加斯奎特。
他最喜欢的绘画地点在山的南线一侧,以勒托洛内村和加尔达纳村为中心。这儿,圣维克多山在村边拔地而起,山上沟壑纵横,生机盎然;松林茂盛,色彩缤纷。而加尔达纳村的兄弟山丘则是眺望圣维克多山的绝佳地点,这里放置了许多塞尚在此所绘圣维克多山画的复制品,看到它们,我仿佛感觉到了画家的天赋。他在画山的同时也把村庄纳入画布——这些画作已初具立体派风格,我久久伫立,把它们与眼前这个金字塔形的山头小镇细加对照,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附近的毕贝姆采石场,塞尚租了一间小屋,心无旁骛地画起人工开凿的砾石,仔细观察每块砾石的形状和色彩,而背景则常常是高耸的圣维克多山。他的最后几幅作品——毫无疑问也是最著名的——都是在劳佛山丘上一条小道的休憩区完成的,离他的艾克斯画室很近。

参观完塞尚的画室之后(我在此向大家极力推荐。画室里的花瓶、水罐和石膏仍然保存完好,仿佛画家只是临时出去一会儿),我沿着塞尚的脚步走向山丘上他最钟爱的创作地。我沮丧地发现这里已经变了模样,但是,当越过树梢看见远处屹立的山峰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分明看到了它因为塞尚赋予的荣光而熠熠生辉。站在那里,我脑中浮现出塞尚最后一次来到此处的情景:67岁的他虽然遇到了雷雨,但仍继续作画。“我发过誓要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在一个月前,他曾对忘年交朋友埃米尔·伯纳德说过这样的话。不到一周,画家死于肺炎。
不过,圣维克多山最迷人的地方无疑是其背面,那里的沃夫纳格镇有一座建于13至17世纪的防御城堡,深挖的地道直通山谷。更有趣的是,对塞尚极其推崇的巴勃罗·毕加索曾是城堡的主人。传闻他在1958年买下了城堡,因为这里是欣赏圣维克多山的一个绝佳地点。可以说,拥有了城堡就真正拥有了圣维克多山。
“1900年,19岁的毕加索简直像只疯狗,”保罗·塞尚协会会员、格拉内艺术博物馆前馆长丹尼斯·库塔涅说,“对任何富有艺术创新的画家他都如饥似渴地去膜拜,去效仿,如图卢兹-罗特列克、安德烈·德朗、亨利·马蒂斯和乔治·鲁奥等。最后,毕加索拜倒在塞尚脚下,自称‘塞尚是我唯一的导师。”
“有一天毕加索告诉我,塞尚就是他的上帝。”菲利普补充道。
总之,毕加索——还有亨利·马蒂斯、乔治·布拉克和让·梅钦赫尔等一众画家——在细心揣摩、研究了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系列以及其他主题的作品后,一头扎进了立体主义,开启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帷幕。
“20世纪的画家在塞尚打开的突破口上砥砺前行,”
丹尼斯·库塔涅指出,“但是每个流派(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只考虑了构图、空间、色彩或透视中的一种元素。塞尚做得更好,他把所有元素统合在一起。他仍然站在世界艺术的最前沿。”
这就是毕加索那句名言回响百年的原因:“塞尚是我们众人之父。”
他所珍视的圣维克多山更是高耸于一切之上。
-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