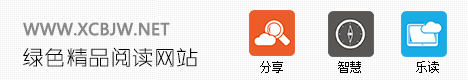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年代。笔者在东北辽宁,那时出门在外,遇到熟人就问:你家大件都有啥?回答:三转一响一“咔嚓”。答者脸上现出自豪的神情,问者也是羡慕不已。何谓三转一响一“咔嚓”?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一“咔嚓”:照相机。这五件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百姓家中的寻常之物,有的早已弃用。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它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具标志性的奢侈品,是最时髦、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小康”之家幸福生活的标志。回忆我家的三转一响一“咔嚓”,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奢侈品”:三转一响
先说“三转”。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城里自行车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上班下班都骑自行车。而在农村就不同了,很少有自行車。人们上镇里赶集买卖东西,只能走路,或坐生产队马车去。我家邻院冯大头卖山货,不知攒了多少年,买了一辆沈阳产的“白山”牌自行车,爱不释手,把自行车擦得锃光瓦亮的,车把、大梁都用玻璃丝缠起来,打扮得花枝招展,五颜六色。记得那年,我有急事去离家30多里的姐姐家,晚上还得赶回家。来回60多里路程,显然徒步走是不行的。我寻思再三,硬着头皮去冯大头家借自行车,并向他保证不损一根毫毛,完璧归赵。还好,他满口答应。谁知道回来时,因路上石子多,加上车技不熟,连车带人掉进沟里,好在沟浅,没有伤人却伤了车,车把擦划了一道痕迹。当我送车时,大头说人没伤着就好,车擦点道道,我用胶布缠上就好了。虽是这么说,但看得出他还是有些不高兴。后来我给他买了一副蓝色毛线织的带穗的手把套,算是赔礼。
那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学校离家仅一河之隔,走路不到20分钟,根本用不着自行车。后来,我在下班后业余时间还给镇上两家企业职工补习文化课。两家企业离家很远,上完课已是夜里10点钟了。为了不耽误时间,需要买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有三大品牌特受人们的喜欢,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天津产的“飞鸽”牌。当时,自行车是紧俏商品,不光要钱,而且还要购物票。这票上哪去弄?我找在清河城供销社工作的亲戚,让他给我弄了张票。正好供销社新进几辆“红旗”牌自行车,130元一辆,就买了一辆。有了自行车,上班,下班,进城,赶集,走亲,访友,出行方便快捷多了。那时谁能骑上一辆新自行车,虽不是名牌,走在大街上都能招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自己也觉得脸上有光。
接下来说说手表,手表算是那个年代的高档奢侈品。记得我们村生产队长是县劳动模范,县里开会时奖励他一块“上海”牌手表,回来戴在手脖上,不时地贴在耳朵上听“咔咔咔”手表转动的声音,心里是美滋滋的,在人前挽起长袖露出手表显摆一下,或自言自语:几点了。再也不用夜里看月亮看星星听鸡叫、白天看太阳看日影判断时间了。上工时他按点敲钟,下班时就以他手表为准。有一天,他忘给手表上弦了,害得大家摸黑才放工。

我在中学教书,常常因课堂上时间拿捏得不准而延课。课间休息10分钟,有时因延时学生只能休息5分钟就又要上课。我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手表也是紧俏物品,需要手表票。好在丹东市供销社有个亲属,通过他在丹东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厂出产的“春蕾”牌手表,这块手表要125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大钱呀!要知道我当时月工资才28元呐!它走时准确,样式美观大方,望着那亮晶晶的新手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块表,现在我还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它还是那样闪闪发光,上满弦依然走得十分准确,成了我一个念想,一个记忆。
我家那台缝纫机是我结婚时托人买的,是大连缝纫机厂出产的“飞马”牌。过去买布买衣服要用布票。买衣服价格贵,买不起,所以大都是自己做衣服。有缝纫机的,用缝纫机做,没有缝纫机的,就得手工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省工省时,针脚均匀,美观好看。缝纫机除了做衣服外,还多用作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缝补衣服是家家户户的寻常事,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我家的缝纫机常招来村里心灵手巧的姑娘、小媳妇。她们用它把旧衣服翻新,把大改小,当然,更多的是做个小孩红兜兜、小裤衩,扎个鞋垫之类。现在都买现成的衣服了,我家那台缝纫机自然也就成了“古董”。
再说“一响”。“一响”就是收音机。我们那都管收音机叫“话匣子”“戏匣子”。60年代初,大部分农村没有电,自然也就没有收音机了。后来办了电,农村有了有线广播,有了扩音大喇叭。家境好的人家开始购买收音机。收音机有南京产的“红星”牌,天津产的“牡丹”牌,上海产的“上海”牌,有带红灯或绿灯指示灯的,有中短波段的,有双音箱的,等等。那时,我的姐夫在市交电公司工作,我家购买了一台“上海”牌收音机。在文化生活稀缺的年代,收音机就成了我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文化生活除了看书写字画画外,就是一年看几次农村放映队下乡放映的电影。自从我家有了收音机后,更多的是收听广播。
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有梅兰芳、马连良、袁世海唱的京剧,有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魏荣元唱的评剧,有侯宝林、马三立、郭启儒说的相声,有李润杰、王印权、高凤山说的快板书,有杨立德、刘同武、傅永昌说的山东快书,有骆玉笙、赵崇义的京韵大鼓,有荣剑尘的单弦,有徐小楼、王悦恒表演的二人转,有袁阔成、刘兰芳等名家说的评书,还有那胡松华、郭颂、马玉涛、郭兰英、王昆等名家演唱的歌曲,等等,百花齐放,叫人百听不厌。在我家集聚的有老人、青年,还有儿童,儿童最爱少儿节目“小喇叭”,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
最后说说一“咔嚓”,也就是照相机。在20世纪70年代,我并没有照相机。那时常见的照相机型号为135,一卷胶卷能照36张。还有一种型号为120,“海鸥”牌相机,方形能照12张,长形能照16张,都是黑白的。
年轻时,很想给自己留下一张青春照,可是没钱去照相馆照。记得有一年冬季,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在西安交大读书,放寒假回家,他带了一个西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山”牌135相机,虽然能照36张,但照片太小,只有2平方厘米,只好放大。记得他给我照了三张照片,一张是在后山一棵榆树旁照的,一张是我与友人在太子河冰上照的,一张是我们送他在南甸火车站月台上照的。现在后山那棵榆树早已不在,太子河冰依在,只是那背景石崖不在了。至于南甸火车站客车早已停运10多年了。每每翻出这几张照片,物非人非,往事如烟,心里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县城机关工作,有了一点经济基础,才花170多元买了一台“傻瓜”相机,算是圆了我拥有照相机的梦。如今人们大都用手机拍照,连数码相机也可以不随身携带了。我那个“傻瓜”相机又成“文物”了。
- 热门文章